提起新中国奥运史的起点,人们总会想到1984年美国洛杉矶的第23届奥运会,想到许海峰以一枚射击金牌实现的“零的突破”。其实,五星红旗与奥运第一次结缘,是在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上。当时,去还是不去,人们议论纷纷。周恩来一锤定音:要去。这是新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后第一次全面参加奥运比赛,也是我国首次参加奥运会。
由于当时缺乏准备,那次奥运会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所以这次“奥运首秀”几乎没有走进大众的视线之中。但对亲历者而言,这次首秀不仅影响了自己的人生,也奠定了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基础。此后,新中国离开奥运赛场长达28年之久。再次出现,已经是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奥会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从1952到1980:新中国奥运征战史(上)》。

1952年2月13日早上,挪威奥斯陆迎来两位风尘仆仆的中国人。年岁稍长的叫盛之白,时任新中国驻瑞典使馆的二等秘书,负责文化事务。年轻人是使馆的翻译谢启美。两人头天晚上10点才从斯德哥尔摩出发,连夜赶到奥斯陆,是为了完成一项前所未有的外交任务。
事情还得从11天前苏联驻华使馆里的一场会面谈起。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是会谈的发起人。客人冯文彬,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中央书记。罗冯会谈的内容并不复杂,罗申告诉冯文彬:台湾已经报名,要参加7月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夏季奥运会,他想知道中国大陆方面是否也愿意派人参加。
当时,新中国的文艺和体育事业由团中央负责。1949年10月召开的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冯文彬当选为主任,荣高棠是副主任兼秘书长。体总的筹备委员会也由团中央直属,代行体总职责。
罗申大使的语气亲切和善又充满鼓励,仿佛不是询问,而是劝导。苏联人的心思不难揣摩。他们已组建起一支实力雄厚的运动队,憋足了劲儿,要在奥运会上与美国人一较高低。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苏联自然希望新中国也能参赛。而关于第15届奥运会,冯文彬并不是头一回听说。1951年3月,芬兰就曾向新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新中国能派选手参加。
但中国有自己的难处。新中国成立伊始,又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参加奥运会的事很难被提上日程。不过,这回苏联“老大哥”发出了诚挚建议,值得再度深入思考。从苏联使馆回来,冯文彬便召集廖承志、蒋南翔、荣高棠等几位团中央领导,一起开会商讨。
几个人的意见出奇地一致:既有主办国芬兰的热忱邀请,又有友好国家苏联的支持帮助,我们当然要参加!竞技体育太容易让人热血沸腾,更何况还有代表新中国参赛的万丈豪情。冯文彬很快起草了书面报告,将情况汇报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很快,周恩来就批准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国际奥委会的电报。
电报中,体总以一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口吻知会国际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根据中国在过去参加历届奥运会的关系,决定仍继续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并决定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及2月15日在奥斯陆举行的奥林匹克年会会议。请即将该会议程及参加会议代表之人数通知本会,以便准备参加。”
盛之白和谢启美此行是受外交部差遣,前往奥斯陆参加国际奥委会第46届年会的。但他们既没有接到会议议程,也没有接到会议邀请。因为奥委会年会只邀请委员参加,其他人根本无权参会。连体总和外交部都没搞明白,盛之白和谢启美就更不知道了。
初到奥斯陆,盛之白和谢启美两眼一抹黑,就连国际奥委会年会在哪里召开都不清楚。两人灵机一动,先联系上与新中国交好的波兰和保加利亚驻挪威使馆。在使馆的帮助下,他们总算见到了苏联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德烈亚诺夫。安德烈亚诺夫态度友善,但说的话好似当头一棒。两位中国访客这才知道,年会早在12日就开幕了,他们根本没资格参加会议。
安德烈亚诺夫告诉盛之白,芬兰籍的奥委会委员已经把新中国参加奥运的请求在会上提了出来。奥委会主席、瑞典人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伦认为,新中国的体总确实可以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但体总在给奥委会的电报中提到“旧的全国奥委会已经瓦解,新的体育组织已经成立,现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入会”等字眼,似乎又在说体总是新成立的组织。
埃德斯特伦的结论对新中国十分不利:既然是新成立的组织,就必须向奥委会重新申请,获得承认以前就不能参加奥运会。从安德烈亚诺夫那里告辞出来,盛之白和谢启美随即拜访了埃德斯特伦,又碰了一鼻子灰。主席果然说,一些国际单项体育总会都说你们这个体总根本没人知道,也从未参加过一次奥运会。盛之白只好将原本准备好的发言稿交给主席,请他转交给大会。发言稿的题目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继续参加奥林匹克组织》。
看来,盛之白和谢启美对体育一窍不通着实令这位主席不满。他不得不花了一个多钟头给自称体总代表的两位“体育盲”讲了许多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必须了解的常识性问题。
14日大会讨论结束,最终结果是将此事交与奥委会执委会讨论,在6月1日前提交讨论结果。执委会还必须在3月15日之前完成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询问,了解他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关系。
安德烈亚诺夫向盛之白提了几条建议:一、必须肯定现在的体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延续;二、要承认组织各项规章制度一如过去;三、承认旧体协曾经参加过的各国际体育联合会,继续保持不变。消息传回国内,大家一片沉默,原来参加奥运会还有这么多讲究。盛之白综合了种种情况,建议:最紧要的是找到过去全国奥委会一两个旧委员,请他们出面与国际奥委会联系。
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时年26岁的熊斗寅第一次站在了未英胡同33号院的门口。这里看似是普通民宅,其实却是体总筹委会的办公地点。熊斗寅这位上海震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原本是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工作人员,现在被调到体总筹委会工作。
跨进院门,经过一段甬道,是一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院子不大,也就20多平方米。南面屋里是新体育杂志社和编译组,竞赛组和群体组在西边,北屋是个会议室,中间有张乒乓球台权当会议桌。东屋还没人用,堆放着各种杂物。熊斗寅正式报到后,头一件事就是大扫除,把东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作为国际组的办公室。就是这座小院、这二十几号人,管理着新中国的各项体育工作。
熊斗寅这位日后的奥林匹克专家当时对奥运会毫无概念。此时,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事已是箭在弦上。2月中旬,体总一收到盛之白反映的情况,马上修订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同时,秘书长荣高棠致函篮球、田径、游泳、足球、自行车等9个国际运动联合会,声明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经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愿继续参加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因为国际奥委会有规定,一个国家的奥委会必须要管辖至少5个奥运会项目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所属的全国单项协会,这是取得合法席位的必要条件。
3月初,体总却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有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所谓的“中国奥委会”早已“存在”了。
原来,早在1951年年初,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经在台湾复会。代理理事长郝更生致函国际奥委会,借口“中国奥委会26位委员中,已有19位随政府迁移到台湾”,要求将中国奥委会会址自南京迁至台湾新竹市西门街147号。国际奥委会竟然同意了这个申请。
团中央、外交部、体总的几位负责人反复商量,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体总系旧体协改组而来,理应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地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根据大家的意见,专门起草了有关参加奥运会的专题报告。3月23日,周恩来转批了报告,批示不能重新“入会”。体总马上致函奥委会表示抗议。
那段日子里,熊斗寅忙得昏天黑地。整个国际组只有他和另一位同事两个人。他们要翻译大量外国通讯社对奥运会一事的有关报道,还要与外交部国际司的同志一起起草抗议的电报和信件,反复解释新体总与旧体协的继承关系,反复强调中国人对体育的热爱和对参加奥运会的企盼,反复声明新中国的体总管辖着全中国的体育事业。但所有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时,有人提起了远在甘肃兰州的一位六旬老人,西北师范学院的一名教授。之前,老人已经从报纸上得知新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和奥委会年会的消息。他当即提笔写了一封信,把他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准备寄给北京的体总。但在信即将丢进邮筒的那一刻,老人犹豫了,又把信塞回了口袋。
熊斗寅记得,那天他跟体总筹委会秘书晏福民赶到前门火车站接站。他们知道,来人是旧中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算个大官。面前的长者头发花白,腰杆挺直,面色红润,一身棕黑色中山装,神采奕奕。他很谦虚和蔼地跟两个年轻人握手,感谢他们特地来车站接他。
这位老人姓董,名守义,是中国奥运史上无法被忽视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是中国奥委会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之一。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另外两位委员王正廷和孔祥熙,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美国,只有董守义一人留在了大陆。有关方面早就想到了董守义,只是鉴于他曾在旧政权身居要职,所以迟迟无法请他出山。这一回,周总理专门指示,由教育部出面将他调来北京。
熊斗寅把董守义安排在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董守义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熊斗寅就多了一项工作。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跑去请教,上午的时间则留给董老休息和备课。多年后,熊斗寅回忆:“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
从董守义热情而耐心的讲解中,熊斗寅第一次知道了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的历史,知道了奥林匹克宪章,还知道了骑在马匹上的比赛项目叫盛装舞步,皮划艇中有个项目叫障碍回旋(现名激流回旋)……董守义还带着一本他在解放前出版的著作《国际奥林匹克》,浅咖啡色封面,32开本,约有200多页,繁体竖排,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董守义当时也只剩一本了,所以熊斗寅一直没好意思开口跟他要。
最令熊斗寅兴奋的是,这位老人提供了外交部和体总方面最渴望了解到的情况。因为他亲身参加过国际奥委会的年会以及1936年和1948年的两届奥运会。
熊斗寅对董老敬佩不已,董守义的大半辈子也确实传奇。早年他曾赴美留学,攻读后来改名为春田学院的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体育系。回国后,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上世纪20年代,天津有支篮球队叱咤风云,号称“南开五虎”,董守义正是那支篮球队的主教练。1947年,董守义担任体协总干事期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不仅带来了知识和经验,也为体总增加了在奥委会说话的分量。只是6月5日就是奥运会报名的截止日期,此时已是5月底,还来得及吗?
此时,体总仍没有收到国际奥委会的答复。台湾方面已于5月19日向组委会报名,决定派出22人组成的代表团。6月4日,在没有收到答复的情况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冯文彬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联名电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中国决定派出游泳、篮球、足球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
6月的北京天气晴好,十几个人正在燕京大学的土操场上飞奔。带球、传球、停球、射门,每个人的身后扬起一阵尘土,裹挟着小石子四处乱溅。他们是在1951年全国足篮排球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各路好手。这些人的名字,今天的球迷未必知晓。但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国家队和各省运动队的总教头,现在足球界、篮球界里的明星球员和教练员很多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
从1952年年初开始,他们被陆续调进北京,参加“中央体训班”的集训。这个体训班由体总副秘书长黄中主抓,目的是培养运动骨干,地点就在燕京大学。体训班初创,条件简陋。他们只能借住在学生宿舍楼的阁楼上。大白天也得开着灯,因为窗户只是开在膝盖以下的装饰品。练足球的倒还好,同住的篮球运动员可就惨了,一进屋就伸不直身子。即便如此,日子却过得其乐融融。
篮坛老将程世春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到体训班以后吃的第一顿饭:“肉沫豌豆雪里蕻,一大铁桶,每人一大碗,馒头随便吃。比我在大学里的伙食强多了。”训练结束后,大家就凑在一起跳舞、演节目。有人会拉手风琴,有人会弹六弦琴,还有人擅长黑管。不少人都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大学生,素质之高,令人赞叹。
运动员们都梦想着世界级别的竞赛场,但事情的发展却没有顺大家的心愿。6月1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伦发表公告,表示国际奥委会希望在来年解决中国问题,现在中国的两个组织——台湾的一个和大陆的一个,均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这项公告引起了双方强烈的反应。董守义亲笔签名,电告国际奥委会:依据奥林匹克宪章,你们无权阻止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
台湾方面的运动员此刻正在马尼拉训练。他们在美国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布伦戴奇的支持下,决定仍按原计划于7月12日正式出发,以显示参赛的决心。这个时候,奥运会的大门其实还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埃德斯特伦主席发布的公告并没有经过执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年会通过。希望虽然渺茫,但还存在。
国际奥委会的最终决定依然难产,有人可等不及了——奥运会篮球比赛的抽签仪式即将开始。篮球是唯一一项海峡两岸均以中国队名义报名参加的比赛,这个签怎么个抽法,成为各方的焦点。时任国际篮球总会秘书长的威廉·琼斯与台湾方面的郝更生和大陆方面的董守义还是春田学院的校友,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琼斯秘书长最后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把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篮球体育总会定名为China,而把台湾的中华民国篮球协会定名为福摩萨。福摩萨是葡萄牙语,是过去欧洲人称呼台湾的用语。对这样的决定,双方都不满意,但琼斯的决定只能遵守。到了真正开始抽签时候,琼斯又故意使两支代表队在第一轮初赛中轮空。这样就可以等待第47届国际奥委会上的最终决定了。
1952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第47届年会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到会委员57名,中国籍委员均没有出席。主席埃德斯特伦任期已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主持年会。在致大会开幕词时,埃德斯特伦提到:“诸位在本届年会中,除了要另选一位新主席之外,尚有许多重要的提案及问题等待解决。”其中就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申请被承认为中国国家奥委会”的问题。
盛之白这一次没有迟到。他在7月13日就赶到了赫尔辛基,并拜访了国际奥委会秘书长奥托·梅尔。这一次,盛之白的身份也与奥斯陆之行不同。他不再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的私人代表。
按有关规定,奥委会委员需得本人亲自出席年会,不能委派代表。但秘书长告诉盛之白,年会已经给予郝更生发言的机会,为了公平起见,可以给盛之白同样的机会。17日上午10时,盛之白接到通知,可以列席会议。他跟翻译谢启美赶紧赶到会议室外等候。他们到达时,郝更生正在那儿坐立不安、来回踱步。
郝更生首先被请进会场。他说,这一次的所谓“中国问题”是荒谬绝伦的。他还自以为是地提出了一大发现:“我对董守义先生的签名很熟悉,跟目前国际奥委会收到的信件上的签名并不一致。”郝更生由此断言,董守义的签名系伪造,绝非出于董守义的自由意志。至于董守义的下落,郝更生打出了“悲情牌”:听说董守义已经失踪很久了,没准儿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郝更生出来后,盛之白大步走进了会议室。主席建议:“让你的翻译直接念英文稿就可以了。”盛之白却说:“翻译只能翻译,不能代表我说话。”主席只好同意:“这里没有人懂中文,可以说得短些。”会场里一阵笑声,气氛反倒轻松了些。在质询中,盛之白坚持体总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组织,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有代表不经意设置了一个“陷阱”:“你们申请入会的手续是否合乎规章的二十五条的规定?”盛之白机智回应:“我们并不是申请入会,我们一向就是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国家奥委会。”
话题最后集中到一个问题上:“董守义为什么不亲自来?”盛之白说,“他要来,目前不来的原因,在他给奥委会的电报中已经说明了。”埃德斯特伦插话:“电报昨天已经读过了,他的要求是驱逐台湾。”埃德斯特伦又问:“这个电报,董守义是不是签了字?”盛之白答:“电报既然是他的私人名义,他当然签字了。”
下午2时,对所谓“中国问题”的讨论继续进行。最后,主席根据大家意见,请委员们就下列两个提案来投票:一、不允许任何一方队伍参加。这个提案由大会执委会提出,获32票附议。二、双方选手们均可参加比赛,但其参加的项目,必须经过各国际单项运动总会的认可。这个提案只获得29票附议。投票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一共53人投票。结果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第二个提案获得33票,第一个提案只获得20票。就这样,大会否决了执委会的提案。
7月18日晚,北京终于收到了一封发自赫尔辛基的电报:“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7月17日会议,我们很荣幸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主席伊利克·冯·佛伦凯。”
奥运会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幕了。去,还是不去?冯文彬、荣高棠、董越千、黄中等人凑在一块儿商量。意见分成了两派。有人主张去:好不容易才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如果不去会影响关系,还会辜负支持我们的朋友的盛情;再说电报上又没有提及邀请台湾的情况,当然应该参加。而荣高棠则主张不去:如果我们去了,台湾代表团也去了,会不会有人趁机制造“两个中国”?再者,新中国运动员水平落后,奥运会上不会有好成绩,会不会给新中国脸上抹黑?事关重大,大家赶紧把意见写成报告,提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7月19日,总理指示终于传达下来了。结果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报告上爽快利落地批了几个字:“要去。请主席、少奇同志阅。周恩来。”众人再一看,毛泽东、刘少奇也已经圈阅。用“炸锅”来形容当时的状况,一点也不过分。
本文摘编自《北京日报》、外交部解密档案《盛之白出席1952年年会的报告》


版权声明:节目版权由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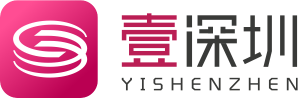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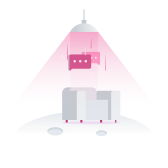 还没有人发言,快来抢沙发吧
还没有人发言,快来抢沙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