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赫尔辛基迎来了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十几天里,近50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100万观众为各国体育健儿呐喊助威。忙碌中,临时组建的中国代表团出发了。多年后,每一位受访者都对周恩来总理的一句嘱托记忆犹新:“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或许他已预见到中国的奥林匹克之路并不平坦,会有屈辱、泪水、失望,甚至愤怒。
1954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年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了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但同时会议又允许台湾以所谓“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义加入国际奥委会。迫不得已之下,新中国放弃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并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断和国际奥委会及9个单项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从1952到1980:新中国奥运征战史(中)》。

距离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召开只有几小时的时候,周恩来的指示终于传达下来。干脆利落的“要去”两个字和毛泽东、刘少奇的圈阅笔迹让气氛瞬间沸腾。在所有亲历者的回忆里,当时完全乱成一片。
个别运动员当时还没有到京,赶紧坐火车赶来。代表团成员赶到当时最有名的“红都”裁缝店,排着队请老师傅量体裁衣。每人做一件咔布丁咖啡色西装上衣,一条舍维呢的灰色裤子,还有一件300号毛线织的毛衣,胸前绣着“中国”两个字。景泰蓝的坛坛罐罐找来了不少,装在礼盒里,准备当作礼品……1952年7月22日,体总正式电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称中国代表队即将出发。
23日,荣高棠、黄中、吴学谦、董守义和篮球队指导牟作云、足球队指导李凤楼在未英胡同33号等了整整一天,哪儿都没敢去。离登机的时间进入倒计时,还剩5个小时,4个小时,3个半小时……电话铃终于响起来,几只手几乎同时伸向了电话机。电话那头,总理叫他们马上赶到中南海。
周总理嘱咐了很多,让代表团不要担心台湾方面,说就算台湾运动员也启程,他们从马尼拉出发,不如我们取道苏联来得便利,肯定是我们先到。总理还细心地提醒代表团,要提早预备好国旗和国歌唱片,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主办方未必能有准备……半个多世纪后,每位受访者都对总理的最后一句嘱托记忆犹新:“总之,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24日清晨,三架小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头一架飞机上以足球队为主:队员马韶华、王政文、汪礼宾、何家统、丛安庆、李逢春、陈成达、张杰、李朝贵、方纫秋、孙福成、郭鸿宾、金龙湖、郑德耀、张邦伦,领队是李凤楼。
第二架飞机上坐着团长荣高棠,副团长黄中、吴学谦,总指挥董守义,总务许庆善,干事郝克强,医生刘明时,游泳选手吴传玉,还有翻译程镇球、王裕禄、康维,以及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当时是代表团的法语翻译。
第三架飞机上都是篮球运动员。领队是赫赫有名的“南开五虎”之一牟作云,队员张长禄、周宝恩、陈文斌、卢鼎厚、王元祺、李议亭、程世春、田福海、张先烈、白金申。
飞机慢慢升高,向着西北,一路飞去。代表团中很多人都是头一次坐飞机,眼瞅着下方的万寿山和颐和园越变越小,兴奋不已。但没过多久,大家就变了脸色。小飞机只能在二三百米的半空中飞行,遇到气流便剧烈颠簸。程世春老人后来形容:“就跟摇元宵似的……”
北京这边飞机一起飞,盛之白便在赫尔辛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中国代表团启程的消息。他特意指出,董守义也将随团前来。据说,郝更生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称:“共产党善于搞政治宣传,他们会用面貌相似的人以假代真,冒名顶替,掩人耳目。”一位英国籍奥委会委员还站出来说:“我跟董先生很熟悉,是真是假,我自有办法鉴别。”几句话说得神秘兮兮,让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代表团充满了期待。
只不过,赫尔辛基的众人须得耐住性子,多等几天。因为小飞机需要加油,遇到紧急情况又得迫降,一路飞,一路停。当看到飞机的舷窗外出现大片的绿色,美丽小岛星罗棋布地散落在海水中的时候,飞机上的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终于到了——美丽的千湖之国芬兰。7月29日上午11时,飞机降落在赫尔辛基机场。大家走下飞机时,奥组委官员、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世界各国的记者们一拥而上。
那位原先夸下海口的奥委会委员挤到董守义面前,说了句:“先生,请原谅我的无礼。”手一伸,就伸进董老先生的衣服里。董守义莫名惊愕,这位英国籍的委员却乐起来:“没错,这是真正的董守义先生。”原来,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知道董守义的腋下有一颗豆粒大小的红痣。结果就想出了这么一招。
大巴车把中国代表团从机场送到了奥坦尼阿米树林,林间空地便是运动员的驻地。赫尔辛基奥组委特意把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代表团安排在一起,与美国等国代表团的驻地离得老远。苏联“老大哥”很热情,一得到消息,马上安排一部分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先期回国,腾出房间,好让中国代表团入住。中国代表团没日没夜地赶路,早已累得人困马乏。但大家一下车,气儿也不喘一口,马上就集合起来。所有人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升旗。
篮球队当时还没有赶到,他们在莫斯科换乘了火车,尚在途中,但顾不了那么多了。于是,晕机症状轻一点的足球选手张邦伦和陈成达担任了旗手和护旗手。当时的照片显示,那面五星红旗似乎是深浅不一的布料拼接而成,而且长宽比例明显不对。据陈成达老人估计,很有可能是使馆工作人员匆匆忙忙赶制的。
伴着缭绕林间的国歌,旗子一点点升起来,终于飘扬在奥运村的上空。这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的殿堂里,奥林匹克大家庭也正式吸纳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仪式上,荣高棠做了简短发言。面对周围的各国记者、国际友人和奥组委官员,他的话铿锵有力:“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终究来到了。我们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与良好的友情。”
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记者们在文章中铺撒了大把的惊叹号。芬兰最大一家报纸报道此事所用标题是《中国选手赶来参加已结束的奥运会》。台湾的郝更生也曾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过这个题目。他认为,这是芬兰报纸对新中国代表团的讽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字里行间又何尝不是芬兰人对新中国运动员“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惊叹!
不过,比赛的确已近尾声,足球、篮球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赶上将于7月30日进行的男子100米仰泳预赛。吴传玉这个名字,不该被遗忘。他是一位印尼华侨,1951年随印尼青年代表团到北京参观,就此决定留在祖国,希望能在游泳赛场上为自己的国家争光。来赫尔辛基的路上,他一路晕机,吐得一塌糊涂,到达又赶上赫尔辛基的“白夜”,天很晚才黑,很早就亮,几乎没有夜晚,以至于难以入眠。所有人都劝他放弃30日的比赛,但他却操着结结巴巴的中文,用最坚定的语气要求参赛。
比赛开始了,吴传玉与英、法、巴西、苏联、葡萄牙、墨西哥的选手同列第5组。他拼尽全力,最终游出了1"12"3,名列第五,没能进入复赛。这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吴传玉的名字因此被载入了史册,被称为“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
8月1日,中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的一家饭店举办了盛大的招待酒会。来自苏联、民主德国、美国、英国的百余位运动员和官员应邀参加,宾主欢聚一堂。在随团干事郝克强的记忆中,几位美国运动员把送给他们的景泰蓝迫不及待地从盒子里拿出来,举在手里看来看去,神情稀罕不已。
8月3日下午,能容纳七八万人的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里座无虚席,助威声排山倒海。奥运会足球总决赛此刻正在举行,对阵双方是匈牙利与南斯拉夫。中国代表团在主席台旁边的观众席就座,跟苏联运动员们坐在一起。代表团万分讶异地感受着人们对体育的热爱和疯狂。程世春当时感慨不已:“这些人看起球来,怎么都跟疯子似的!”
终场哨音响起,比赛结束了。扩音器里传出话来,请各代表团旗手入场参加闭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篮球运动员张长禄、护旗手陈文斌。两人当年都是一米八几的个头儿,气度颇为不凡。但张长禄实在是太紧张,以至于多年以后,这么重大的一件事,细节他竟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他说,“没办法,我的精神全集中在旗子上了,检查旗杆有没有问题,旗子系紧了没有,万一飘不起来怎么办?哪有心思东看西看。”
入场的顺序是按照各国国名打头字母排序的。如果按照英文排序,中国应该靠前,但按照芬兰语的字母排序,中国正好排在了中间。当各国旗手依次入场,面朝主席台围成一个半圆形时,五星红旗恰好位于最中心,鲜艳夺目。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完成了既定的任务。
回国后,8月21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举行了第二次常务会议,听取了荣高棠关于中国代表团参加该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和今后如何加速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建议,并进行了热烈讨论。会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共中央呈递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成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这个意见很快获得了批准。1952年11月15日,体委正式成立,贺龙担任主任,蔡廷锴是副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此时, 体委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9月,“政务院”改称“国务院”,体委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
赫尔辛基奥运会闭幕一年后,1953年8月4日,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友谊体育比赛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体育场开幕。吴传玉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游泳比赛,并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游出了1"06"4的成绩,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竞技体育比赛中的第一枚金牌,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体育大赛的最好成绩。遗憾的是,1954年10月,吴传玉在赴匈牙利学习途中因乘坐的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遇难时年仅26岁。
从赫尔辛基带队归来后,董守义历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主任、运动司副司长等职,是第二、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78年以83岁的高龄去世。
在团组织工作的何振梁作为随团翻译奔赴芬兰赫尔辛基,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体育之路。这个“历史的误会”是他与奥运一生结缘的开始。
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荣高棠,在1954年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值得一提的的是,乒乓球能成为中国的“国球”,是与荣高棠早期的努力分不开的。1952年,荣高棠参与创建了中国乒乓球队。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罗马尼亚第20届世乒赛。布加勒斯特的弗洛利亚斯克体育馆见证了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这是中国乒乓球选手第一次登上世乒赛的舞台。尽管当时成果不算辉煌,但中国乒乓球队此后五十年笑傲世界乒坛的恢宏画卷正是由此展开。
1954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年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了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台湾体育界的郝更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痛哭流涕地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反而复杂起来。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布伦戴奇未经全会讨论,悄悄地把所谓“中华民国”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其后,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仿效国际奥委会的做法,在国际体育界制造出“两个中国”的问题。新中国迫不得已放弃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并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断和国际奥委会以及9个单项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此后,新中国离开奥运赛场长达22年之久。
虽然长期被隔绝在主流国际赛事之外,但中国一直没有放弃努力。1972年5月,国家体委的一份请示文件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时任国家体委国际司干部张清说,周总理的批示极为细致:“第一个,原则同意,第二个,要有步骤地开展,第三个,不要造成我有求于人的局面,要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地来做,不要急于求成。”
转机发生在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资格,并提出只有台湾被驱逐,才会重新参加奥运会。举办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加拿大政府,于1970年开始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所以提出,如果台湾打算以中国的名义参加,将拒绝其参赛。一些国际奥委会成员表示出震惊和不满,强烈要求取消该届比赛,但最终奥运会还是如期举行了。加拿大政府顶住美国的压力,最后以台湾代表队在赛前收拾行囊打包回家而收场。
1977年秋,国家体委的工作重归正轨,我国的对外交往逐渐恢复正常。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都十分紧迫。1978年,国际奥委会在突尼斯举行执委会。东道主的体育部长在贺词中说:“难道人们可以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整个大陆而同时相信奥林匹克运动是世界性的吗?”
对这一议题,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显然早有准备。会议前,他就曾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说明其对台湾地位的态度。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回信说:“就联合国而言,根据联合国大会1971年10月25日的第2758号决议,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联合国的立场促使基拉宁朝着更坚决的方向前进。他向执委会报告了自己在1977年9月的中国之行。不过,仍有许多委员不希望台湾的运动员被排除在外。“找个过渡办法”的重担,落到了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萨马兰奇肩上。
1978年4月,萨马兰奇一到北京,就显示出“工作狂”的性格。他对翻译说,他是为工作而来的,礼仪性的活动就让夫人参加吧。何振梁以中华体育总会常委的身份担任萨马兰奇的全程陪同,他俩著名的友谊就是从这时起开始的。萨马兰奇后来说,“我那时想不通,一个有着10亿人口的大国,居然不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国。这个决定实在是太奇妙了。”
何振梁夫人为其撰写的传记中披露,萨马兰奇对何振梁说:“最彻底的办法是通过投票驱逐台湾,但这存在失败的风险。虽然国际奥委会的85个委员中只有8个人的政府与台湾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但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绝大部分持独立立场, 不受政府影响,所以表决的结果难以预测。”萨马兰奇认为,从策略上来考虑,可以提出要求台湾改名的方案。他估计台湾不会接受,这样国际奥委会就可以予以除名或者停止会籍。然而,这一方案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毕竟,中方参加商谈的人没人敢拍这个板。
1979年对中国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这是1980年冬、夏季奥运会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年。国际奥委会将在年内举行一次全会和五次执委会。能否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将决定我们能否于次年参加奥运会。
这一年,在国际政治和对台关系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一天,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倡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的对峙状态,呼吁两岸间尽早实现“三通”。中央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相应的,重返奥运的努力也有了更多的运作空间。
1979年2月,一份谈话记录传到体委,让何振梁大受鼓舞。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时,被问到:“1980年将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中国是否有意参加或将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邓小平回答:“首先要解决台湾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们要成为奥运会的成员,中国正在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奥运会四年一次,1984年、1988年都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是1988年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行奥运会。”
连重返奥运都困难重重,邓小平却信心满满地提出,要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举办奥运会。这对何振梁来说,简直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有小平同志“撑腰”,两个月后,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何振梁在答辩中即使1对80“舌战群儒”,也毫不怯阵。当时有委员提出来,体育跟政治无关,不要在这种场合发表政治言论。对方有挑衅的意味,何振梁沉着应对:“先生,首先你问的这是政治性的问题,我必须以政治性的语言来回答你。”类似的问题不计其数。两年之后,萨马兰奇对此还记忆犹新。他对何振梁说:“你在蒙得维的亚会议上对各种提问的回答,赢得了委员们的尊敬。”
何振梁答辩离场后,委员们通宵开会,讨论台湾应该改用什么名称。其实,早在1960年的旧金山会议上,国际奥委会委员乔治·瓦尔加斯就曾提议:“为什么不把‘中国’和‘台湾’放到一起,就叫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可惜,国际奥委会用了20年才想起采用这个精确的名字去解开长期的僵局。
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79年10月的名古屋会议上获得了回报。“名古屋决议”决定: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确认中国奥委会的会籍;并在改名、改旗和徽、改歌的条件下,同意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保留其会籍。这就是所谓“奥运模式”。作为“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领域里的具体化,之后各个国际体育组织都按照这一模式处理了台湾的会籍问题。
从1951年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算起,这场在国际体育界维护“一个中国”的斗争,整整斗了28年。消息传到北京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庆祝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豪迈地说:“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走上了世界体育舞台。”
国家体委说干就干,1979年便进入“奥运模式”,指示各省将赢得奥运比赛这一集体目标作为体育发展的指引,1980年又推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新口号。
事已至此,台湾当局仍在耍花招。对“Chinese Taipei”的中文译名,北京坚持叫“中国台北”,而台北偏要译成“中华台北”,一字之差在两岸之间引起激辩。台湾代表吴经国回忆,讨论了快一年,最后还是邓小平拍板才接受了台湾的翻译。纠葛一直绵延到1989年,中国允许台湾使用有争议的“中华台北”名义参加1990年北京亚运会。萨马兰奇对我国如此大度非常感激。他在许多场合都说:“台湾问题所以能顺利解决,完全是由于中国的宽宏大量。”
本文摘编自《北京日报》、外交部解密档案《盛之白出席1952年年会的报告》


版权声明:节目版权由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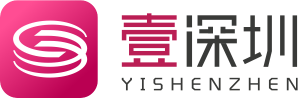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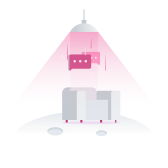 还没有人发言,快来抢沙发吧
还没有人发言,快来抢沙发吧





